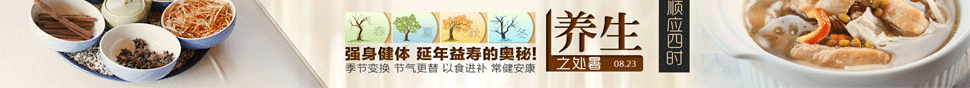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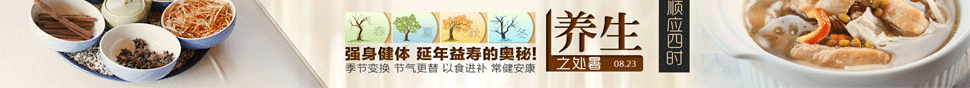
文张卓娅
与黎锦光初次见面,李香兰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那是年初秋,黎锦光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也就是今天那座“小红楼”)里录制唱片,休息时,他走出密闭的音棚呼吸新鲜空气,忍不住点燃了一支香烟。此时南风吹来阵阵花香,远处还有夜莺在啼唱,这美妙的时光,引起他的乐思涌动,他一时来不及寻找纸张,就在那盒香烟纸的背面,信手写下了简单的旋律,接着填词、修改、直至完成。于是,这样一首具有欧美风格、伦巴节奏、舞曲样式的《夜来香》便悄然诞生了。起初他拿给了周璇、姚莉等大牌歌星试唱,但因为这首歌音域太宽、有近二个八度,她们唱不了,只得作罢。
(衡山路的“百代小红楼”,是孕育了“夜来香”和一代音乐巅峰之作的殿堂)
也是机缘巧合,这天,24岁的日本籍女歌手李香兰,来到百代公司录制一部影片主题曲,无意中在黎锦光的桌上见到了《夜来香》的歌谱。一试唱,顿时欣喜若狂:这正是她多少年梦寐以求的心曲!从此,《夜来香》随着李香兰唱红了中国、日本、东南亚和世界,其歌碟先后出了86种版本!
李香兰身世复杂,本是日本血统(名为山口淑子)却生于中国,曾为关东军献唱却又以中国人自居,年她刚唱响《夜来香》,第二年抗战胜利先是以“汉奸”罪名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来却发现她是日本公民而遭遣返。战后,她以日语演唱的“夜来香”简直风靡了万千日本歌迷,年甚至借由歌迷的支持而选上了日本参议员。当然,对于黎锦光先生的感恩怀念之情,她从未忘怀,“文革”结束后,她曾想方设法邀请黎锦光访问日本,会见歌迷,但是很难,很难,大家懂的。
(因为文化身份的暧昧模糊,李香兰得以在中日夹缝之间以歌声出道)
黎锦光告诉我们,直到年7月(也就是我们到访他家前不久),借着在日本举行一次纪念聂耳中日友好活动的由头,李香兰全力争取了主管统战部门领导的支持,方才使他能够在女儿的陪同下访问了日本。这真是一次“梦幻之旅”——歌迷的簇拥、李香兰的盛情、堂皇富贵的居所……令黎锦光心潮难平。他对我们说:“她(指李香兰)活得像皇后一样,而我就像地上一根草。”
临回国前,李香兰想帮衬恩师一些钱,黎锦光没敢要,被整怕了:“我怎么敢从日本拿钱回来?一分钞票都不敢拿的。李香兰最后没办法,就送我一个大电视机和一套高级音响做礼品,我坐船回国带回家的。”当他说出这些故事,我们便理解了他急于出手这些“洋货”的原因——他急需要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啊。
黎锦光老师的才能真是名不虚传,他为唱片厂写的配器,一听就不是“样板戏”时代的,相反与港台的流行曲很接近,特别是打击乐的运用,当时在国内很少有人懂。他的耳朵太好了,听一盘盒带马上知道谱子是怎么写的。我们的专辑录制工作很快就开始了,棚里录音的时候哪一只乐器的音准、节奏有一点问题,都休想逃过他的耳朵。“文革”中他家里的钢琴被抄走,始终没有拿回来,而我只有一件事搞不明白:家里没有了钢琴,他给唱片厂写配器怎么定和声呢?他说出了秘密:“我每天带着谱子步行去唱片厂,在走廊里有架钢琴可以用,我听一下和声很快的,不用求别人。”这是怎样一种强大、平和的内心在支撑他?是音乐给了他力量!
听这他些话,我心里直发酸。他以七十多岁的年龄,以其成就和才华,真不该受如此的委屈啊。就在这个阶段,一个“黎粉大侠”出现了。当时我们住在附近的海军文化工作站招待所里,工作站是负责向海军各部队发放、供应文化娱乐器材和组织业余文化活动的单位,站长姓什么我忘了,且叫他“莫站长”吧,也是一位乐迷。一天他听我们说,正在请黎锦光给我们录音,激动万分地说:“哎呀,他是我最崇拜的偶像啊,他还活着吗?我还藏有一张他的唱片‘送我一支玫瑰花’呢!”——没想到莫站长居然和我私藏了同一张胶木版的老唱片。
莫站长要跟我们一起去“拜见”黎锦光。于是,我们就带着这位海军站长去了黎锦光的家。可是一见到这简陋破落的小屋、地上的破洞,尤其是见到黎锦光消瘦苍老的面容,这堂堂军人男子汉竟然哭了!他拉着黎老先生的手,什么也说不出来……可以想象,当他听说李香兰送的音响电视需要出手时,简直就像听到了军令状一样,回到单位立即利用他在文化器材行业的人脉,为这套音响寻找一位出价最高的买家。当时的“进口电器”还是很走俏的,莫站长成功为黎老师换回了不少生活费,让我们十分欣慰的是,从此站长和黎老师成了忘年之交,每个星期都请他吃饭,请他讲课,连续接济他的生活好多年。
我的《林涧清泉》专辑,在黎锦光老师的监制之下成功完成。前后十多天时间,我们这些音乐后辈从他那里汲取了极其宝贵的养分,在他那个破旧的小屋里,我们俩还请他给我们讲了几堂轻音乐配器课,分析他写的谱子,收获巨大!为我们一年多后创作的成名作歌剧《芳草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剧中的一曲《小草》歌也广为流传。我那时才明白一件事:七、八十年代风靡大陆的港台流行歌曲,并非凭空创造,原本就是传承了当年上海的“时代歌曲”,也就是以“黎氏兄弟”、陈歌辛等为代表的那一代音乐人的成就。
(年黎锦光与李香兰在东京相见,照片模糊却弥足珍贵)
年对于黎锦光而言,是重新迎来“生命之春”的年代。唱片厂很快为他恢复了待遇,更重要的是,他直接参与和指导了对上海三、四十年代“时代金曲”的修复、挖掘与再现。仿佛是命中有缘,我自小一起长大的亲密伙伴陈海燕,恰在这时结识了黎先生。一段忘年之交,成就了“夜来香”最后的一段传奇。下一期,我就请海燕来“浮生场”,继续给大家讲黎锦光的晚年故事,讲“夜来香”由年轻一辈再次唱响舞台的传奇。
(陈海燕文章待续)
浮生场习惯在电脑上看文章的朋友
也可以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jiulixianga.com/jlxzz/1338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