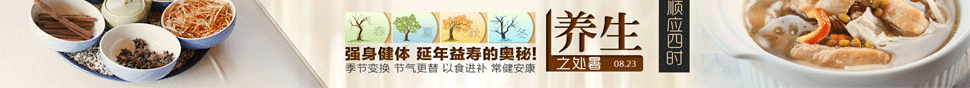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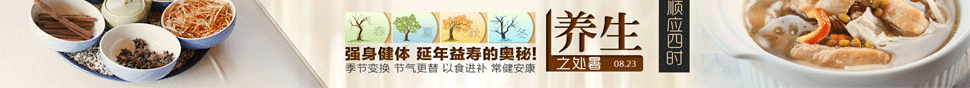
《攀援的凌霄花》
——关于《艾菲布里斯特》的读书报告
18级德班水渊天
0
在中国人的概念里,有个浪漫的词叫作“藤缠树”,它暗喻着男女间的深情,即缠绵难分、至死不渝。后来有个女性用诗句发声,她不愿做攀援树木的凌霄花,而想做一株独立的木棉,追寻平等的爱。这使我想起德国作家冯塔纳的小说《艾菲·布里斯特》,书中女主人公的名字“艾菲”有常春藤之意,而男主角的名字“格尔特”意为一种欣长挺拔的树木。
小说《艾菲·布里斯特》的故事并不复杂。十七岁的美丽少女艾菲活泼单纯,由父母做主嫁给了母亲昔日的情人殷士台顿男爵,婚后随夫去往荒凉落后的波罗的海海滨城市凯辛生活。殷士台顿年长艾菲二十一岁,追求名利、公务繁忙,被冷落的艾菲既感寂寞孤独,又受惊于公馆中的“中国鬼魂”。在与殷士台顿的友人克拉姆巴斯的交往中,艾菲与其发生恋情。七年后,殷士台顿偶然发现此事,为捍卫名誉,决斗枪杀克拉姆巴斯,与艾菲离婚,并教导女儿疏离母亲。艾菲被退婚后,不被父母接纳,直至身患重病才被允许回娘家居住。不久,她无望地死去。
艾菲的故事就像是对于藤缠树故事的另一种理解,即藤与树不再脉脉温情地代表共抵生死的缠绵,而是体现了一种依附关系。我不免产生好奇,是什么让藤与树在这个故事里以悲剧收尾的呢?
01
树与藤
十七岁的妙龄少女,美丽单纯又脆弱,名为“常青藤”的艾菲就像是一藤凌霄花。她一方面是个活泼、单纯、大胆的女孩,富于想象,沉浸于梦幻世界;另一方面,她也被教导得现实而虚荣。艾菲看似很容易感情强烈,对神话、绘画、自然颇感兴趣的浪漫自由的人,可她对自己的婚姻表现出的态度并不太积极。她说首先要爱情,其次是荣华富贵和名誉,最后是娱乐和消遣。但要是得不到温存和爱情,她就会喜欢财产和舒适的房子。她是很乐于与殷士台顿的婚事的,就像她喜爱最高档的精品,殷士台顿无疑是个很合适的结婚对象。婚姻于她仿佛不过是进入社会的筹码,在小说世界里,年龄以及对方作为母亲旧情人的身份都不是衡量是否相配的重点,相配的标准只在于是否有贵族的身份、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漂亮的容貌。就像牧师太太评价这门亲事时说的,不过是名门攀旧户,乌龟爱王八的道理。
可以说,艾菲在父母的教导下,已经是个努力适应生活的孩子了,可她的悲剧性命运也与其格息息相关。青涩的年纪和浅薄的社会经验使她在社交方面遭遇波折,年龄差距大而又忙碌的丈夫,既让她有些怕,又令她深感孤独。她对情感的敏感与渴望,使她易被克拉姆巴斯引诱、挑拨。这种渴望与内心道德相冲突,又使她易被鬼魂与羞愧困扰。就像她的母亲忧虑的那样,艾菲缺乏坚定意志,斗争和抵抗不是她能胜任的。艾菲是个活泼爱自由的女孩,喜欢出游、自然,出于善心收纳失业女仆罗丝维塔。可她是被束缚住了的,面对命运的波折,她虽感到痛苦绝望,却只是消极地听天由命。
更不幸的是,青涩的艾菲像是一只初入草原的羔羊,是个易被看透的人。艾菲的妈妈说她脾气未免有些古怪难猜,可这些小心思的难猜,并不代表她大体的难懂。父母知道她的不坚定,能猜测她的婚姻状况。殷士台顿敏锐地知道艾菲的想法,只是不肯用轻率的举止赢得爱情。克拉姆巴斯能一步步引导艾菲的思绪。在西多妮一类人的眼里,艾菲这样一位年轻的太太也是易懂的。
成熟稳重,有了一定社会地位的英俊男爵,格尔特·冯·殷士台顿便是艾菲选择的橡树了。这棵橡树非常符合长辈们的要求,稳重包容,又追求事业,势必能青云直上。订婚时的殷士台顿四十岁,脾气好,地位高,前途好,品行端正,聪明人都看得出这是个良配。艾菲的父母想,他温厚,懂年轻人的心理,是个能包容年轻任性女孩的好人选。“你们结婚以后,要是他仍然保持这种多为别人着想的优点,那你们的婚姻就够美满的了。”布里斯特太太如是说。这样一个正派的人,不免古板保守。汲汲于名利的他,忽视了新婚妻子的感受,使艾菲感到孤单恐惧。正派刻板的他,即便爱着妻子艾菲,不憎恨其曾经的不忠,却也一定要为捍卫名誉而战。在发起决斗挑战前,他与友人维勒斯多夫进行了一番交谈,清楚地分析了利弊,知道一旦发出挑战,一生的幸福就双倍地葬送掉了。尽管如此,他仍不听友人规劝,毅然做出决定,因为他有一定要这么做的理由,他的原则要求他捍卫整体的利益和名誉。维勒斯多夫无奈地指出,这个社会名誉的崇拜是一种偶像崇拜,只要这个偶像一天还起作用,就得向它顶礼膜拜。殷士台顿为此不在乎自己的幸福成为泡影,决斗杀死克拉姆巴斯,与艾菲退婚,教导女儿成为合乎规范的冷漠正派的人。此后的他也不快乐,内心空虚的他开始质疑功名利禄的意义,曾经死守条文不放的他终于明白,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不择手段追求“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幸福无异于捕风捉影,他的悲剧与艾菲的悲剧交织在了一起。
生长在茂密的树林里,高大的树木投下浓重的阴影,这是个美丽而又竞争激烈的世界,阳光和养分是那样有限,怎么才能更好地活着呢?一棵蔓草离开父母的庇护,当然要缠住一棵强壮的树木,攀援着它,享受这可贵的特权。森林里的每株植物都是那样做的,这株凌霄花当然也要选择这么做。财富和地位毕竟是少数人享有的东西,一旦一代人得到了就不愿放手,而是想办法固化它,把这难能的养分和资源延续下去,婚姻的缔结大概便是最理想最便捷的方法了。这大概是那个社会的法则,艾菲所处的环境如同一片密林,丛林法则要求她融入束缚与条文。艾菲初嫁时,社交并不熟练,不足以应付作为县长太太的社会角色,她的社交初试可以说并不成功。她那时想,如果是母亲应对这些的话,一定迎刃有余。可是,与此相矛盾的是,在这样的选择题里,年轻女孩不是陪伴一个年轻的丈夫成长,随着青年成长成熟为壮年,与他新婚的妻子需要一段磨合期。克拉姆巴斯也像是这丛林里的危险诱惑,他风流老道,引诱艾菲出错越轨。这阴森森的林子里还有无情的风,像无数人的口舌,无孔不入,它是林子里的规矩,将出了错的藤蔓吹落,出了错的植物吹断。
艾菲的父母也可以看作是一对树与藤,艾菲的母亲在年轻时舍弃爱情,嫁与布里斯特先生。当他们有了孩子之后,也为这孩子挑选了一份最好的安排。在他们的观念里,身份、财富和名誉是社会规范所看重的择偶标尺,贪图享乐、爱好虚荣一类则是些无伤大雅的东西。这对父母无疑是了解孩子的,艾菲的妈妈从与孩子的零碎谈话中立即能捕捉到有效信息——这情形像极了我的父母,他们也能从我的无心言辞中立即推断出我内心状况;她虽忧虑年轻的艾菲不太懂事、有些自负,若是不爱殷士台顿,婚后生活难免糟糕,却还是为艾菲敲定了这门婚事。这对父母无疑也是爱孩子的,可对社会名誉更为重视,因而直至被退婚的艾菲病重之际,才接纳其回家。小说结尾,失去爱女的布里斯特太太疑惑艾菲的死是否父母的过错。布里斯特先生回答说:“这是个太广阔的领域”。也许在其他很多时候,布里斯特先生的这个回答不过是对疑问的搪塞之词,然而,面对结尾的这个问题,的确可以说这是个太广阔的领域。过错究竟在谁,父母教育的错、艾菲的脆弱不忠、殷士台顿的刻板冷漠、克拉姆巴斯的浪荡,还是许多人固守的某些观念的错?这的确是个太广阔的、延伸到书外的领域。
02
简练叙述下的暗涌
长篇小说《艾菲·布里斯特》结构紧凑,情节基本成单线发展,呈现出较明显的明暗线双线结构。明线即故事明面的情节走向,艾菲的婚姻生活悲剧,依据艾菲与殷士台顿婚姻的开始、过程和破裂展开。明线情节大致可细分为一下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婚前,交代艾菲和殷士台顿的情况,缔结婚姻的考虑及态度。这一部分还交代了艾菲及其父母和周边人对这段婚姻的看法。有关不幸的不忠妇女的歌谣、快速的婚姻确立、父母对艾菲的忧虑,这一切都奠定了故事的悲剧基调。
第二部分为艾菲婚姻生活的磨合期,这段过程持续较久,大体时间为婚后直至离开凯辛。殷士台顿刻板(不浪漫),忙于公务,使艾菲感到受冷落。社交场合的不顺,加之阴森房子中鬼魂的刺激,换房子的要求遭拒,使得艾菲终日不安,心惊胆战,在克拉姆巴斯的引诱下出轨。这为艾菲的婚姻悲剧埋下伏笔。
第三部分为婚姻和睦期,艾菲随夫举家迁往柏林,开始新生活,逐渐融入家庭和社会角色,成为一个相夫教女的合格太太。
第四部分为婚姻破裂,殷士台顿偶然发现缠绕红线的信件,发起决斗,杀死友人克拉姆巴斯。艾菲被退婚,夫离子散,不被父母和孩子以及世俗环境接纳,郁郁而终。殷士台顿的幸福也随之成为泡影。我们不知道艾菲为什么不选择像《混乱与迷惘》中男主人公博托那样烧毁信件,而是宁愿将缠着红线的信件保留下来。这些信就像是隐藏在平静生活下的催命符,像她出演的剧本《一步之错》一样,只要错走一步,就每一步都不再被原谅了。
对于故事情节的发展,我感受最深的是其叙述的详略有别。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困惑自己是不是借错了书,怀疑自己读的是删节本。在作品的开头和结尾,作者用自然清新的文字详细描述布里斯特家位于霍恩克莱门邸宅的景色。而关于艾菲定亲、怀孕、私通等很多情节都是一笔带过或是表述隐晦。特别是有关与克拉姆巴斯交往部分的描述,直到七年后殷士台顿发现情书之时,才真正把这段情感点破。
暗线则是指人物情感的发展。我读到一个说法,即认为小说的暗线是艾菲夫妻与“中国鬼魅”关系的心理线,以“中国鬼魅”是否出现为标志,鬼魂在作品中存在的基本线索大致表现为“想像——在场——缺失——又在场——缺失的在场”这样一种时隐时现的结构关系。我觉得这是个立意很好、很值得了解的观点。
实际上我在阅读过程中,并没有把中国鬼魂摆在很重要、与连贯性有关的位置来进行思考。所以,此处我只简单地把这段婚姻中的心理发展认作暗线线索,其他一切都只是助动力而已。艾菲在婚前对这段婚姻的看法是期待认可,却又不乏畏惧。殷士台顿也对婚姻表述认同,他到了合适的年纪和地位,要娶一位合适的妻子了。
婚后初期,面对陌生的环境,忙碌的丈夫,不太适应的社交世界,神经紧张的艾菲被阴森房子里的中国鬼魂困扰。需要说明的是,这时的鬼魂对艾菲来说并无特殊意义,她知道的仅是这是个死去的中国人,葬在海边。后来得知中国鬼魂是殉情而死,这反倒使她不再畏惧它。殷士台顿忙于各种事务,虽然对艾菲表示出体贴包容,但教条的他并不理解妻子的孤独和对鬼魂的害怕。
有了女儿安妮后,艾菲的孤独仍然没能得到缓解。在与克拉姆巴斯的交往中,她开始对丈夫产生怀疑——猜测丈夫想用鬼魂来教育她。心绪动摇的艾菲被更为浪漫自由的克拉姆巴斯吸引。出轨后的艾菲内心不安羞愧,逃离凯辛,去往柏林。看似重新开始的生活,因约翰娜带来的中国人贴纸和无意间发现的克拉姆巴斯村而埋下心结。当一个人心绪放松的时候,怎样的暗示都影响不到她的心情。但当一个人极度不安时,风声鹤鸣都像是致命的追兵。中国鬼魂和与克拉姆巴斯的过往阴魂不散地追来,艾菲即便表现得若无其事,平静的冰面下也还是出现了裂纹。这时的中国鬼魂也不再只是那个殉情的中国人(因不被社会认可的爱情而死),这时刻提醒着艾菲曾有的私情。殷士台顿觉察了好友与妻子的交往过密,曾经提醒妻子,却不会因此做出改变,以便挽回妻子的爱。
逃离凯辛后,艾菲的心情开始趋于平静,度过了很长一段和睦的婚姻生活。七年后,曾经的私情暴露,婚姻破裂后,艾菲的心情痛苦并消极自责,在被亲人和女儿抛弃后彻底绝望。只有仆人罗丝维塔和洛洛的善意给了她最后一点温暖和谅解。她临死前终于与自己和解,做出了灵魂世界最大的反抗,她的不幸罪过在于理智冷酷、斤斤计较的殷士台顿,是他坚守的旧道德、旧秩序将她置于死地。不过,艾菲最终还是认同了这样的殷士台顿及其做法,原谅了他,从而实现了人格的高贵和伟大。殷士台顿在经历了心理纠结抗争后,心中维护名誉的一半战胜了保留婚姻幸福的一半。家庭破裂后的他,虽觉得功名与幸福是过眼云烟,但还是将这“喜剧”演到底,走着名利之路,教导孩子成为“正派”的人。
03
矛盾的冯塔纳
读完整本小说,我的第一反应其实是迷茫。有好朋友问我这本书讲的是什么,我能描述出故事情节,但我很难去给里面的每个人物“定个性”。大部分时候读文章,你可以很快很精准地概括人物的大体特征,比如善良正直,邪恶狡猾。
我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我不能毫不犹豫地说,艾菲是追求爱情与自由的勇士,是对教条的反叛者。她喜欢享乐与荣华,其实很愿意嫁给殷士台顿,因为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和婚姻,只是天真地完全相信父母只会对她好,为她做的安排肯定也是好的。她和克拉姆巴斯之间并不算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她顺从于社会,并没有反抗旧制度,她死前将悲剧的根源归咎于冷漠的殷士台顿,却没有看见殷士台顿身后迫害她致死的对名誉功利万分维护的世界。
我不能说殷士台顿是个刻板保守的冥顽不灵者,是加害者。他正派、包容、有风度,离婚后不幸福的他,看淡名利和幸福,对虚伪的教条有所醒悟。可若要说他是个醒悟者,他却又执意要把这悲剧演到底。
我不能说是克拉姆巴斯是美好、自由、爱情的象征。他有对自由的追求,甚至可能有些对社会束缚的不屑和洒脱,但他更像是个感情上的狡猾的骗子。他风流成性,爱与女子交往,一步步用挑拨、暗示等方法引诱艾菲出轨。他风月场老手外表下隐藏着的究竟是严肃认真,还是不愿意承担这份偷情责任把感情斗争进行到底,情愿与世俗道德和现实要求相妥协的懦弱?
面对上述种种困惑,我的猜想是,一般可以较为提炼出人物关键性格的作品,是作者的情感倾向或写作目的比较明确的。创作者有较明确的褒贬观点,即使表面不显,也会通过塑造相应的人物来表达观点和意向,通过书中人物之口表达己意。而《艾菲·布里斯特》这本书中人物的矛盾点,很有可能就是作者冯塔纳思想矛盾点的折射。冯塔纳出生成长于十九世纪的德国,这一阶段的德国社会局势混乱,政权变迁频繁,思想繁杂。冯塔纳本人的思想不断发生着变化。
《艾菲·布里斯特》创作于其晚年,以俾斯麦统治时期为时代背景,描绘的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封建军事帝国时期的故事。这一时期的冯塔纳已从民谣作者转变为普鲁士制度的批判者。他的创作主要矛盾点在于,一方面企图维护与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紧密联系的传统思想和社会规范;另一方面,他批判贵族们虚伪的道德和病态追求虚名的社会。冯塔纳是制度的批判者,痛恨着虚伪的道德和社会,但他又偏袒着一些与旧制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传统观念。这使他陷入混乱与迷惘中,是他一时跳脱不出的思想闭环,也许当时的他,心中有一把不太明晰的秤。因而,书中人物形象显得颇为复杂,故事里每个人都有些过错,每个人都在追悔反思,每个人都比原来对灵魂多领悟了些,但好像没有一个人彻底想清了什么。小说里的每个人都像是牺牲品。艾菲郁郁而终,布里斯特夫妇失去女儿,克拉姆巴斯决斗失败被杀,殷士台顿家庭破碎……一对对因利益名誉而结合在一起的树与藤,他们故事在这样一个冷漠的世界里就注定难以美满了。
撰稿:18级德班水渊天
指导老师:杨劲
编辑:Roe
图片来源于网络
初审:游小红老师
审核:凌曦老师
审核发布:杨劲老师
中大德语系
投稿信箱:
sysu_deutsch
.

